中國,人們把情商的重要性提升到了一個可望而不可及的高度,往往與道德一起,成為罵人中“先發制人”的銳器。哪怕是一個聰明的人,如果沒有情商,十有八九是不行的,也會被貼上桀驁的標簽。在各種雞湯文的推波助瀾之下,情商成為了一個人是否能成功的必要條件,左右逢源能說會道乃至會忽悠的人就叫做“成功”;而沉默寡言淡定安然過日子的人卻成為了“不成功”的象征,會被人各種嫌棄,各種無視。在現代社會,大家似乎默認了笑貧不笑娼、喜鬧不喜靜的生活狀態,只要有錢有權有美色有數不完的應酬就好,誰都不喜歡平靜而淡定的活著。

情商往往與道德一起,成為罵人中“先發制人”的銳器
這種浮躁的現象,恰如一面貼著壁紙的華麗墻壁,沒人在乎背后充塞的是臟皺的泥坯和煩亂的線團。這是人性,也是現實,所以喜歡瀑布者多,喜歡深潭者少,喜歡大海沙灘者多,喜歡高山峻嶺者少,喜歡吹牛斗氣夸夸其談者多,喜歡沉默寡言者少。這個世界,人們大多數選擇的是熱鬧和表面,而不是淡定和從容,所以女人才會折騰外貌,男人才會拼搏事業,一切的一切,似乎又是這樣的自然而然,無需分辯。
可實際上,熱鬧的人卻并非真開心,孤獨的人也未必真難受,否則“獨處是一個人的狂歡,聚會是一群人的孤獨”就不會被大眾所認同,也就不會有這么多的外向型孤獨癥患者。這就引申出了另外一個問題,追求大眾的認同是否值得去努力包裝自己,或是帶上面具。

熱鬧的人卻并非真開心,孤獨的人也未必真難受
古今中外,這個世界上總有些桀驁不馴的天才會用自己特立獨行的風格給予回應:能用智商就能輕松碾壓你們這群渣渣的我,為什么要努力去提高情商來適應這種不舒服!
情商,一個外來的、誕生不足百年的新詞并沒有如同智商那樣被理解得干脆利落和深入人心,因為這個詞不是被理解為世故,就會被理解為城府。
情商的真正含義被埋沒了,它的本質其實是指能控制自己情緒和他人情緒的能力。一個情商高的人,會敏銳地覺察到自己乃至周圍人情緒的變動,并能通過語言和肢體表達來引導和擴散,比如負面的情緒能夠當即化解,快樂的情緒能夠傳染到周圍等等,自身情緒很少會有失控的現象出現,總會恰到好處的自我解決。
情商不是外來詞匯,中國古已有之,現在我們不過是把貓叫成咪咪罷了。儒家早就說過“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說,各種情緒在將發而未發的時候叫做“中”,而發的恰到好處則叫做“和”。有了中和以后那就厲害了,“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因此,孔老夫子就將“中庸”兩字提高到了無比高的位置,“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后世儒家干脆就將之列為《四書》之一。
中者,庸之道也。中庸者,情商之道。“中庸”之道即為提高情商的方法。儒家自古就認為,人不光要努力學習,還得不斷提升自己的情商。中庸后,儒家做的不是“和稀泥”的芝麻蒜皮小事,而是治國平天下的大事——“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可見,先秦儒家的確是有大丈夫之風的。

中庸者,情商之道
可惜,儒家后來不想做大丈夫了,干脆實行自我閹割以明志,不要中,只留庸,越庸越好,結果致使腐儒泛濫,中國人的氣節也隨之不斷下滑。
膽小,畏畏縮縮,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各掃門前雪,麻木不仁,行尸走肉……
腐儒把中國人一步步變成了魯迅筆下最痛恨也最無奈的那種人。而這種人的后代,從腐儒搖身變為“知識分子”,還在教育下一代:我們要龜縮,繼續龜縮,不要露頭,這樣可以活很久……
“中庸”二字,逐漸成為了無能和龜縮的代名詞。
氣憤之余也有些悲哀。
之所以會成這樣,只因“庸”還在,而“中”沒了。中就是平衡,就是底線,就是原則。“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天地為陰陽,陰陽相合相離,氣息相交而生萬物,而萬物相輔相成,又形成了一個完美的大自然生態鏈。完美,則中和。陰陽不平衡,在自然界會發生動亂,在人體則會生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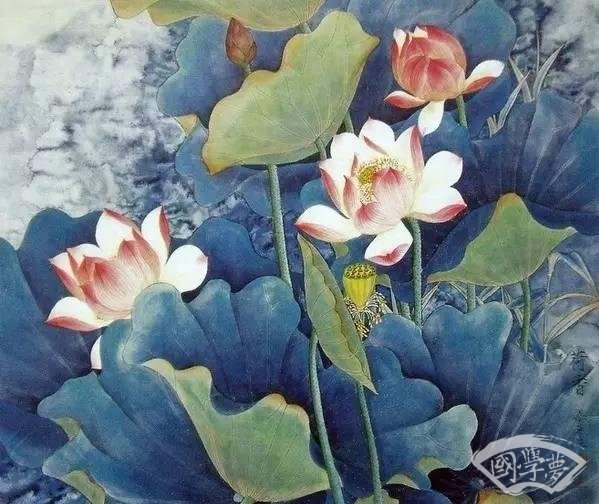
中就是平衡,就是底線,就是原則
心清靜而自獨,眾人清靜則為和。情商的關鍵在于控制自己的情緒,調整他人的情緒,和緩大眾的情緒。這才是真正的“中庸”。如果一味學“腐儒”作踐自己,沒了“中”,沒了平衡,沒了底線,沒了原則,那遲早會出事。所以,情商的高低不在于是否獨處,也不在于一味追求別人的認同和追求熱鬧,否則儒家何必又提“慎獨”。
心清靜,致中和。平靜而淡定,是一種“致中和”的自然狀態,也是一種不需要外在認可而內心自我“圓滿”的境界。在儒家看來,真正達到“中庸”的人是一個有操守、有底線、有原則的大丈夫、真君子,一個真正關心天下的愛國者才是“真儒家”!
關鍵詞:中庸